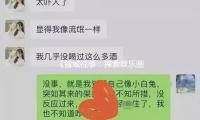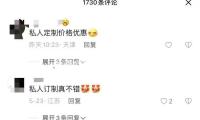不愧是最巨大的美剧,它改变了全部电视规矩
近日,娱乐圈内多位明星的黑料被曝光,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料,某知名艺人在私人生活中出现了不当行为,而其团队迅速否认。这一事件虽然尚未得到证实,但已引发了众多评论,大家纷纷探讨这些黑料的真实性与可能的后果。此类事件再次提醒公众,明星的光鲜外表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起
「美人的逝世是国际上富有诗意的论题,」爱伦·坡说。
1990年,一具被冲上岸的归于选美皇后的17岁美艳尸身,不只打乱了剧中双峰镇的安静,也引发了美国商业电视领域的一场风暴。
一、收视率vs.急进美学
大卫·林奇的《双峰》以其共同的美学风格,对美国商业电视剧的深层规矩,构成了一次洗脑般的冲击。
《双峰》首位季收视率之高出人意料,美国约三分之一的电视受众(3500万人)收看了这部剧集。首位季的成功,被谈论界解读为大多数电视受众脱离传统电视俗套的缄默沉静的独立宣言(理查德·狄恩斯特语)。

《双峰》首位季(1990)
可是,更具有大卫·林奇美学风格的《双峰》第二季,遭受了收视率大跌,最终简直达到了黄金节目的收视底线(但仍然有800万观众),这一丧命失利终结了电视领域的这次美学革新。
但不行否认的是,大卫·林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商业电视引进了不相同的美学元素,让美国电视业看到了某种改动的或许性。

《双峰》第二季(1990)
《双峰》是对传统商业电视剧方法的一次仿照与推翻。在方法上,《双峰》借用并融合了几种干流电视剧方法——侦察剧、肥皂剧与喜剧,但又全然不同于任何一种。
有谈论乃至以为,《双峰》将一手改动电视自身。尽管这种以为《双峰》将要在电视业带来审美革新的观念传达颇广,但也有谈论以为,第二季被砍的命运,证明了急进美学在群众文明产品中的必定失利。
第二季完毕后,《双峰》的联合制片人马克·弗罗斯特在《纽约时报》上直爽而尖锐的声明:我以为它一点也没有改动电视。这多少也暗含了一种情绪——关于群众文明产品的保存与不行撼动性的某种无法。

《双峰》第二季(199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双峰》的命运与其由公共电视台(ABC公共广播电视网)出品的特点密切相关。首位季的美学立异被约束在必定鸿沟内,但又为烦闷的商业电视剧集带来了新鲜的风格元素,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第二季愈加天马行空、怪力乱神,将首位季中偶尔出现的梦境变成一个巨大的梦魇,其艺术性与不流畅性逾越了群众文明产品的美学领域,遭受滑铁卢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电视这种保存的群众传达媒介而言,传达方法决议了美学方法与传达受众密不行分——公共电视台受众的数量,使著作有必要满意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气。
只要传达媒介的改动,才有或许带来受众集体观影方法与审美兴趣的改动。我以为,直到后来有线电视频道HBO、Showtime、AMC以及流媒体网站Netflix出品了电视剧《前方》《黑道宗族》《绝命毒师》《真探》等,才逐步改动了美国电视剧集的美学方法。
二、浅显叙事vs.笼统美学
尽管有联合制作人马克·弗罗斯特的加持,平衡了大卫·林奇的不流畅与天马行空,但《双峰》仍是一部典型的大卫·林奇风格的电视剧。
可是不得不供认,首位季的成功,来自于在商业剧集的保存与美学立异之间的平衡。

《双峰》把浅显肥皂剧与侦察剧奇妙的混合在一起。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秘、三角恋、越轨、社区邻里联系这些肥皂剧主题,被侦破案子这一侦察剧的中心戏曲动作串联在一起。既引发观众在观看侦察剧时一探终究的好奇心,又撩拨观众关于肥皂剧家长里短的八卦喜好。
大卫·林奇原本就拿手使用商业叙事元素,齐泽克以为林奇是一位前拉斐尔派的作者——将前锋探究与庸俗艺术交叠在一起。
谋杀、诡计、暴力、金钱、越轨、爱情、乱伦、性这些商业电影招引群众的法宝,被通通放进这部剧集。尽管由于公共电视台的特点,性、暴力、凶杀这些元素以一种隐晦的方法展现,但仍是满意了观众的窥探愿望。

那个起催化剂效果的奥秘事情——谁杀戮了劳拉·帕尔默?当然是招引观众的中心隐秘。可是,跟着剧集打开,这一悬念融入空气中,把很多人物与头绪串联在一起。这些人物与他们的隐秘如此扑朔迷离和具有搅扰性,好像每个人都是嫌疑犯,每个人都有罪,都与劳拉之死有关,但又好像并无联系。
整个小镇似乎忽然之间变成一个巨大的迷局——卡夫卡式的白日梦魇,一切都反常实在却又荒谬古怪,实际主义混杂着奥秘性。地理环境阻隔的世外小镇双峰镇,由于这一出人意料的奥秘谋杀案子,变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
大卫·林奇与马克弗罗斯特画了一张小镇的地图,以这张地图而不是故事,打开他们的剧情——一种全景图的方法建构出双峰镇的社会面貌与人际联系网。差人的查询与人物的日常日子交叉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全体。

原本躲藏的、疏离的社区联系网络,遽然变得可见了,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环环利益相扣、交织着各种愿望的人际联系网。
可是,《双峰》的魅力和超凡之处,又与这些浅显叙事元素无关,而是这些元素以一种大卫·林奇式的奇怪美学风格出现的方法。
《双峰》的创造来自大卫·林奇脑海中的一个意象——一具尸身被冲到岸上。这一意象提醒了大卫·林奇的美学特征——美丽与奇怪、奥秘与日常的混合,就像《蓝丝绒》开场那个田园诗般的小镇与草地里那只腐朽的耳朵。

《蓝丝绒》(1986)
剧会集充满了许多大卫·林奇式的带有超实际感的意象:工作桌上的巨大鹿头、白色的马、几何图形地板的赤色房间、锯木厂的流水线、山崖边的大饭店、甜甜圈、咖啡、生果派、挺拔的枞树、伟人、跳舞的侏儒、对着木头说话的原木女士、停尸房闪耀的灯、赤色窗布。
这些意象,既具有实际质感,又有一种超实际的意味。这种矛盾性,来自于大卫·林奇著作中实际与梦想国际的彼此拉扯与彼此融合——《迷失高速路》《穆赫兰道》《内陆帝国》都是叙述梦境与实际的羁绊与倒置。
而那些奇怪的舞蹈,则常常成为实际国际与梦想国际的分割线——劳拉的父亲利兰那神经质的舞蹈、赤色房间里侏儒的舞蹈。

《内陆帝国》(2006)
与林奇的电影著作相同,《双峰》在情感的表达上适当杂乱,在黑色幽默与悲悯、反讽与诚挚、恐惧与甜美之间摇晃(詹姆斯·纳雷摩尔语)。比方劳拉葬礼上痛哭的利兰与上上下下的棺木升降机、或许在罪案现场忽然哭泣的警探带来的荒谬喜感。
一起,这部剧集吸收了黑色电影的元素——美人之死、犯罪团伙、侦破案子、偷情、谋财害命,但更重要的是,《双峰》引进了黑色电影的心思元素——心思方位或指向的消失。一切都堕入一个巨大的隐秘傍边,变得不行靠与失真,正因如此,第二季完毕时FBI捕快库珀才会堕入一种不可思议的张狂。
三、隐秘与谎话——《双峰》的两层性
法国哲学家瓜塔里在《电影手册》的一篇文章中,把大卫·林奇称作是最巨大的精力病导演。
《双峰》相同具有这种精力病症的割裂特质——一切的主题与人物都变成了两层的,好像片名的两座山峰。
每个人物都具有某种两层性,不管是精力割裂导致两层品格,或是躲藏隐秘导致的两层日子——劳拉(人见人爱的甜心/淫乱吸毒的问题少女)、父亲利兰(丧女的沉痛慈父/乱伦杀女的凶手)、侦察库珀(依托推理的理性/信任梦境和前兆的理性)、木厂主遗孀娇西(娇弱无助的寡妇/心狠手辣的杀夫者)、木厂主姐姐凯瑟琳(白人妇女/日本男人)。
每个人都有两幅面孔——面具与面具之下的、内涵躲藏与外在暴露的,都过着一种充满隐秘与谎话的两层日子。

《双峰》第三季(2017)
人物联系也具有两层性。在这个看似传统保存的小镇,每个人都在越轨,都处于两层联系中。劳拉的揭露男友巴比和隐秘情人詹姆斯、诺玛的情人和老公、雪莉的老公和情人、娇西的两个情人、大亨本与娇西和凯瑟琳的情人联系,连小副角警局接线员露西都有两个情人。
人物设置上也保存了两层特性,建构了多组二元敌对的人物。外来的FBI库珀/本地警长哈里、精明镇定的印第安警探/慌张软弱的白人警探、金发劳拉/黑发表姐曼迪(由同一人扮演)、放纵的劳拉/纯真的唐娜、少女感的唐娜/妩媚的奥德丽、浮躁的巴比/缄默沉静的詹姆斯、侏儒/伟人。
这种精心设置的两层性,构成了故事全体的奥秘气氛,观众跟从人物,进入一种在实际与梦境鸿沟徜徉的梦游状况。
四、杀手鲍伯——意外闯入的资料
杀手鲍伯不管对情节提醒仍是《双峰》不同寻常的恐惧基调来说,都成了至关重要的中心地点。可是,这一人物却是以一种意外的方法进入故事。
大卫·林奇原本的剧本中并没有设置这一人物,某次在现场拍照,偶尔看到布景师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激发了林奇的创意,他就让布景师作为艺人出演了鲍伯这一人物。

鲍勃
这种将偶尔性元素归入著作中的创造方法,来自于大卫·林奇一以贯之的奥秘主义风格。
但需求特别指出的是,《双峰》中这一意外人物的参加,又具有文本承受层面的重要效果——调和了大卫·林奇的主题与干流商业故事之间的抵触。
本来的故事设想中,杀戮劳拉的凶手正是她的父亲利兰,他与劳拉的乱伦联系是劳拉蜕化的罪恶根源,也是他出于张狂的吃醋杀戮了劳拉。
大卫·林奇与马克·弗罗斯特深知,这一凶杀案的本相,关于保存的干流电视媒体而言,是一个无法被受众承受的道德忌讳,这一隐秘会得罪美国干流社会的清教徒价值观。因而,他们在一开始推销试播剧集时,并没有向电视台高层走漏凶手是谁。

而当大卫·林奇意外引进鲍伯这一人物时,问题便方便的解决。
在一个典型的大卫·林奇式的心思惊悚故事中,利兰的乱伦行为必定来自于人物精力割裂发生的凶恶自我——一个内涵紊乱的故事。
但《双峰》中,鲍伯作为一个具有实体的外化形象,将精力割裂的另一重凶恶品格具象化了,成为一个超自然、能够附在不同人物身体上的外来恶灵,这就将心思惊悚的内核转化为一个带有超自然元素的灵异故事。
所以,忌讳的乱伦故事,就被转化为一个邪灵附体的故事。观众能够这样解读,即利兰的乱伦是被邪灵控制了身体和精力,这个人物自身是好的。

可是,咱们有必要意识到,尽管大卫·林奇的电影以奥秘、不流畅著称,但他一向的主题是一种人物内涵的精力紊乱,从《迷失高速路》到《穆赫兰道》《内陆帝国》,都是精力割裂的产品。
尽管林奇常常装神弄鬼,却一向并没有走向超自然力气。林奇的故事本质上仍是更挨近希区柯克的《惊魂记》《迷魂记》,是一种精力病症的外化,而不是《闪灵》《驱魔人》这类超自然的邪灵故事。

《迷魂记》(1958)
可是,电视剧集的群众文明特点,使大卫·林奇不得不保存这一人物的两层性与含糊性,让故事的读解变得敞开。鲍伯这一人物具有某种两层性,既能够是内涵魂灵又能够是外在表征,既能够是人物精力割裂的幻想、也能够是故事中一个实在存在的邪灵。
文明研讨学者理查德·狄恩斯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点评《双峰》前两季的胜败:或许电视在从头承认自己的规矩之前,只能吸收这么多的电影叙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