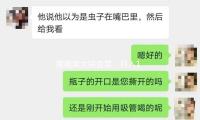当海子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分 — 新京报
近日,网络上流传出一则关于某知名人物的黑料,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与热议。这些信息来源于多方爆料,内容涉及个人生活、职场秘闻等多个方面。虽然真伪尚未得到证实,但不少人对此表示关注。近年来,娱乐圈一直存在各种内幕消息,如何对待这些“吃瓜”事件,考验着公众的判断力与理性思考。


《诗的音讯,诗人的故事》,张新颖 著,上海文艺出书社2024年9月版。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或许是海子的诗里边撒播最广的一首。有人为它谱了曲,唱成了歌;它被选进几种版别的中学语文教材。有的人只读了海子的一首诗,便是它。
这个秋季,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讲课,其间一门是“近二十年来的我国文学”,专门讲一次海子的诗。原本规划的教学大纲里主要讲《麦地》《春天,十个海子》等著作,上课前一周,遽然想起让助教把《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找来,分发给选课的学生。我其时的主意是,这首诗简略,明亮,亲热,或许有助于拉近学生和诗人的间隔吧。
仅仅预备让咱们读读就过渡到其他著作的这首诗,没想到却引起了很有意思的评论。有西班牙血缘的美国学生Anne Rebull问,这个自杀的诗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或许反过来问,写出这样的诗的人怎么会自杀?这首诗写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三日,两个月之后,三月二十六日,海子就在山海关卧轨而死。一个我国台湾出世、美国长大的女生说,为什么他的夸姣里边没有做老板、赚大钱?
我自己也发生了疑问。或许这首诗并不像外表那么“浅显”?对这首诗的情绪过于草率了?
夸姣,其实便是“尘世”的夸姣。
这首诗为人喜欢,是喜欢它的开阔和洁白;喜欢它在这么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境地里,散发着暖融融的、新鲜的夸姣气味;喜欢它对夸姣的界定,是这么单纯、根本。人的夸姣认识或许越来越杂乱、精微和装修化了,对它的寻求越用力,反倒离它越远。夸姣或许就在那些简略、一般却根本的工作之中,或许便是那些工作本身,便是“喂马,劈柴,周游国际”,“关怀粮食和蔬菜”,便是和他人愉快共处,“和每一个亲人通讯”,“陌生人,我也为你祝愿”。

《小森林 夏秋篇》(2014)剧照。
“粮食和蔬菜”,作为关怀的目标,作为夸姣的元素,呈现在这儿,对了解海子诗的人来说,感觉是十分天然的;不过需求特别注意的是,这儿呈现的是土地上成长的食物的大类,而不是详细的、特别的物种,不是海子再三写到的麦子和麦地,更不是“我则站在你苦楚责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苦楚的芒上”(《答复》)的麦地。“粮食和蔬菜”,一般、一般、中性的大类,夸姣需求的正是这样没有尖利性的、能够容纳许多东西的大类,不需求共同的与个人经历、认识、情感紧密联系的详细物种。“粮食和蔬菜”确实是海子关怀的东西,在这儿,却把独归于他个人的认识和感触放置了起来。
“和每一个亲人通讯/告知他们我的夸姣”,这儿触及夸姣的可交流性,可共享性。夸姣是能够说出来的,是说出来之后其他人立刻就能够了解和了解的;夸姣是能够传递的,是在传递过程中不光没有损耗并且还会添加的东西,不仅是传递给了他人,并且使传递夸姣的人愈加夸姣。
那么,什么样的夸姣是能够说出来、能够传递的夸姣呢?明显,独归于个人的认识和感触的东西,具有精力尖利性、排斥性的东西,要说出来、要传递,都会遭遇到交流和共享的困难。海子在这儿所说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用来开端一部巨作的名言,“夸姣的家庭个个都类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不幸是有特性的,而夸姣没有特性,夸姣是类似的。
接下来,海子说得更了解了,夸姣,其实便是“尘世”的夸姣。对陌生人的祝愿,愿他有一个绚烂的出息,愿他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他“在尘世取得夸姣”——这其实是祝愿的套语,乃至能够说是滥调;但是,夸姣不便是这么“浅显”吗?你所要的夸姣,咱们所要的夸姣,不便是这样吗?

《海滨的曼彻斯特》(2016)剧照。
海子祝愿一切人都取得“尘世”的夸姣,他自己呢,只需其间的一点点:“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决议做一个夸姣的人。
“从明日起,做一个夸姣的人”,这个简练爽性的语句,好像是说,做一个夸姣的人,不过便是一个决议,我决议了,那么就能够了,“从明日起”吧。
是什么使他做了这么一个决议呢?从诗的外表,找不出满足的头绪。但这一句,“那夸姣的闪电告知我的/我将告知每一个人”,隐含了重要的信息,尽管信息并不清晰。“夸姣的闪电”是什么?是在他本身内部发生的,比如是他思维中的一闪念,但这个想法遽然照亮了他精力中的漆黑?仍是从外部奇观般来临到他身上的,比如一次出人意料的爱情,一会儿照亮了他暗淡的日子?或许也或许是,这“夸姣的闪电”根本就没发生,但他渴望着被这样的“夸姣的闪电”击中?不管怎样,这个“夸姣的闪电”(即使是幻想中的)使他感触到了夸姣,并且决议传递夸姣,决议做一个夸姣的人。
这首诗的新鲜之感,源于这个决议,有了这个决议,就与曩昔一刀两断了,“从明日开端”,就有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新的国际,这个新的自我在新的国际里做曩昔没有做的新的工作,然后树立起一种新的自我与国际的联系,明显,这是一种和顺的、令人愉悦的联系。
不能把这种联系的树立看成是个人向国际退让的成果,而是说,有了一个新的自我,然后才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姓名”,这个命名的行为,是一种原初的发明行为,是使一个国际开端的行为,是赋予这个国际某种性质的行为。如同是,在此之前,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没有姓名,“我”给它们取一个“温暖的姓名”,它们便是“温暖”的了。

《小森林 夏秋篇》(2014)剧照。
看起来,这首诗里的“我”是温柔的、亲热的,没有棱角和矛头,没有挑战性,没有责问的苦楚和激愤,他与国际的联系改进到了如此精巧的程度,其实不是。这个国际不是实际的国际,而是他自己发明的国际,他在这个国际里能够做他快乐做的任何工作,从“喂马,劈柴”,到“周游国际”,从“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姓名”。在这样的国际里,他当然无须一触即发。他决议做一个夸姣的人,就能够做一个夸姣的人。
有“一个粗野而哀痛的海子”。
他决议要的,一个新的自我和一个新的国际,什么时分能够呈现呢?很快,就在眼前,便是“明日”。
但是,为什么要“从明日起”?为什么不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他如同是一个没有前史的人,他的前史要“从明日”才算起;他的现在,也如同不存在。
但是,仍是不由得要问:现在的“我”,“明日”到来之前的“我”,是什么样的?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里?他和这个国际的联系怎么?
这些问题不能问,一旦问了,答案也就在那里了。他不是一个夸姣的人。他也没有和每一个亲人通讯,他不是一个长于交流的人,他没有能够传递和共享的夸姣告知他们。他被困在他自己的精力苦境里。他也不或许经过重新命名国际就改动国际。
没过多久,在他自杀前十几天写的诗里,他幻想,春天,十个海子复生;但是便是在春天,在这个“做一个夸姣的人”所神往的“春暖花开”的时节,仍是有“一个粗野而哀痛的海子”持久地熟睡——。
在春天,粗野而哀痛的海子。
就剩余这一个,最终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季,倾慕逝世。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无而冰冷的村庄。
(《春天,十个海子》)。
这首诗本身或许是“反着说”。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令人发生夸姣幻想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不安靖的要素,隐藏着要挟着这个美丽国际的要素。反向阅览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这些要素。但是,咱们为什么要去触及乃至去追查这些要素呢?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败兴呢?咱们为什么要逆着这首诗去读,而不是顺着这首诗去读呢?
海子这首诗本身,或许便是“反着说”的,那么假如咱们“反着读”,刚好却是顺正了。
为什么他会在自杀前不久写这样一首诗呢?有一位朋友和我通讯时谈起过这个问题。几年前我编选的《我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书社,二一年)出书后,她以为应该把海子的这首诗选进去。我现在想起来,就写信去问她对这首诗的详细意见。谈到自杀和“夸姣之诗”的联系,我觉得她说得十分好,抄写在这儿:“首要,海子当然知道,或许有时也仰慕,尘世的夸姣;不过我想他没有得到。其次,是不是在那段时刻,他的精力压力现已很大,所以写了这首诗,像一份保证书,或许一种心思暗示,为自己找一个时间短的出口。或许也只要在诗人本身状况和写出来的文字之间存在一个如此巨大的反向拉力的情况下,那些夸姣而空泛的祝愿——愿你有个绚烂的出息,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才能够被了解和接收。在祝愿国际的时分,他也祝愿自己。或许他要的是一种摆脱。这就像一首在失望的时分唱起的赞美诗,假如其间有失望,那一定是完全的失望了。”。

《海滨的曼彻斯特》(2016)剧照。
不过,了解“失望的时分唱起的赞美诗”,能够把焦点放在“失望”上,也能够放在“赞美诗”上。也便是说,咱们仍是能够顺着这首诗来读。咱们仍是能够从正面来承受这首诗。咱们仍是能够供认这个明丽的国际和夸姣的承诺。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以为:做一个夸姣的人便是一个决议,假如我决议做一个夸姣的人,就有或许做成一个夸姣的人?海子没有做到,或许是因为海子太信任自己是一个“粗野而哀痛的海子”了;但这或许并不应该阻碍海子诗的读者,那些广阔的一般读者,去信任一个决议的力气,去测验一个决议的完成。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姓名”,不值得试一试吗?
给自己取一个温暖的姓名——“从明日起,做一个夸姣的人”,不值得试一试吗?
海子大约没有想到,他的诗会撒播得如此广泛,乃至读他的诗的声响,回响在“熟麦的卷发”“海水的眼睛”之间。他从前幻想收麦时节的月光普照下,“咱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飘动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预备吃饭”。他还这样说,“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有钱人/纽约和耶路撒冷/还有我/咱们三个人/一起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麦地》)。这些,也是我课堂上的学生们火热评论的论题。
从校园走到密歇根湖边,仅仅十几分钟的路。面朝望不到头的蓝色水域,我常常忘记了这是湖,而当成了海。这个模糊好像不完全没有道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五大湖相互衔接,我后来知道,地理学家们称之为“北美地中海”,或许是“内陆淡水海”。事实上,即使是“淡水海”的湖,也仍是与海不同,能够找出这样一种差异:这儿短少大海的潮腥味。不知道海子有没有见过海,至少他没有长时刻在海滨日子过,这是必定的;我遽然想,当海子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分,他的幻想里,有没有大海的潮腥味呢?
本文选自《诗的音讯,诗人的故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一切。已取得出书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张新颖。
摘编/何也。
修改/张进。
导语校正/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