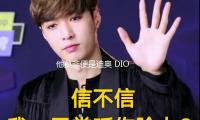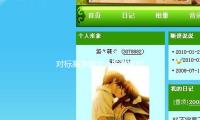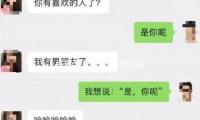她是最巨大的作家,也是最尖端的编剧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明星的黑料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些消息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相关细节已在社交媒体上造成了热议。许多网友开始对事件背后的真相进行掀起讨论,猜测与分析层出不穷。无论如何,这样的爆料都提醒我们,在追逐娱乐新闻的同时,也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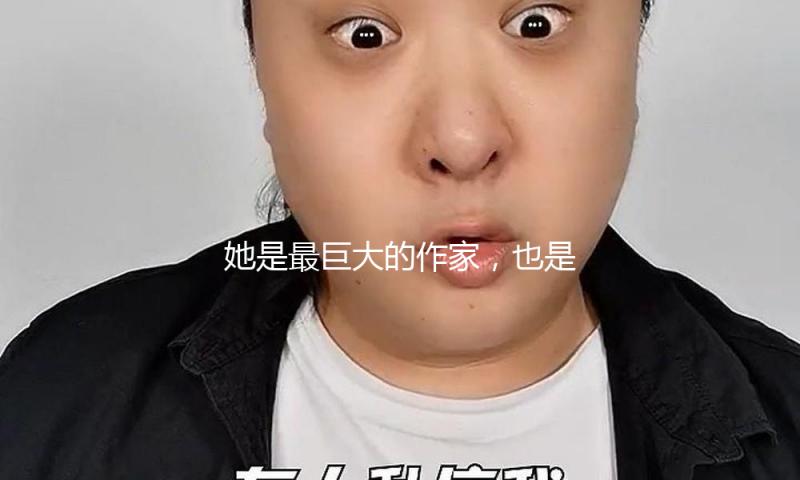
王宇平
(留念张爱玲逝世三十周年。)
1960年由香港电懋公司出品的影片《六月新娘》(唐煌导演,张爱玲编剧,葛兰、乔宏主演)叙述待嫁新娘汪丹林的「婚前惊惧症」。关于行将到来的大婚,她疑虑、犹疑、逃避、落跑……其间遇到两个鲁莽的寻求者:菲律宾华裔青年林亚芒和自旧金山归来的船员麦勤。

《六月新娘》(1960)
关于这两位的热心攻势,汪小姐说出了她心底根深柢固的隔阂:「林先生,你从小在国外,底子不懂得我国的女孩子」、「麦先生,你在国外待久了,关于我国女孩子的心思不大了解」,林先生立时气急败坏,那儿厢麦先生则添了段一见钟情的表达,汪小姐竟「笑得前仰后合」,说「我想你外国电影必定看得太多了,实践上不是这么回事」。
谈爱情时着重「我国性」的闻名人物有留德学生童世舫、英国华裔范柳原,还有「最合抱负的我国现代人物」佟振保,他留学英伦的一大收成是能以我国人、华裔、杂种人和西方人来区别女人。宣称「女人总有女人的庄严」的汪丹林也参加了这支军队,友人们的「最终一分钟解救」将她送回了未婚夫董季方的婚礼红毯。

《六月新娘》(1960)
这种爱情习性足以让电影院观众席上张爱玲的读者会心一笑,况且在丹林逃婚的人仰马翻之际,镜头遽然就给了窗外的明月,「今日晚上的月亮偏偏这么好」,「他们也不知道在哪看月亮」,林亚芒这不可思议的抒发清楚便是:「欢迎来到张爱玲的国际!」董季方赶忙拉上窗布、遮住月亮,让剧情回归了正轨——这是编剧张爱玲的一点自嘲,也是她有意无意留下的个人记号。
编剧张爱玲和小说家张爱玲颇不同,其笔下文字直供大荧幕,借了艺人肉身给演出来后,怎么看都不那么张爱玲,观众/读者全凭忠心和慧眼识出那些记号来接头。张爱玲自己也说,「写文章是比较简略的事,思维经过铅字,直接与读者触摸。
编戏就否则了,内里牵涉到很多我所不明白的不一杂乱的力气」。从充溢掌控力的小说家到面临「不一杂乱的力气」的编剧,张爱玲还有种剧本焦虑叫作「能读不能演」。她与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导演桑弧协作的影片《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大获成功,多少劝慰了这种焦虑。

《太太万岁》(1947)
1952年7月,张爱玲以完结学业为由,脱离我国大陆,南下香港。1955年,她承宋淇之邀进入国际影片发行公司(1956年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成为剧本编审委员会委员;而她正式为「电懋」编写电影剧本,则在她1955年末移居美国之后——这大约与其老友宋淇在1956年公司改组后出任制片主任,掌管剧本的选取和确定有关。
张爱玲并非编剧新手,但电懋公司的编剧环境是另一番六合。跟上海文华影片公司比较,电懋公司资金雄厚、规划更大,但其片厂制约束了编剧的自动权,这就意味着张爱玲的个人颜色将在电影出产中被大大削弱。
在文华公司时,张爱玲的固定协作者是导演桑弧;而在电懋公司,虽然制片主任宋淇要求导演尽量不要更改她的剧本,但她一向短少一个安稳的直接协作者。片厂制又与明星制相连,剧本内容组织天经地义服务于明星形象。

桑弧(中)
此外,就张爱玲自己的实践情况而言:她担任编剧有为「稻粱谋」的火急诉求,且其时已身在美国,大部分剧本都是在写完后邮寄回香港,除了与老友宋淇进行剧本评论外,她与影片导演及艺人短少进一步沟通。
上海时期的张爱玲很乐意谈文学与电影的差异、谈自己的「忐忑」与「思索」,那时的她还站在摩拳擦掌的自动方位上;而在电懋时期张爱玲那里,已然深化到详细的电影出产环节中的她就只需牵涉详细影片的详细问题了,它们散落在她与宋淇的很多通信中。

张爱玲
张爱玲电懋时期的编剧著作,按影院上映时刻依次为:《情场如战场》(1957)、《人财两得》(1958)、《桃花运》(1959)、《六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一曲难忘》(1964)和《南北喜相逢》(1964);此外还有胎死腹中的《红楼梦》与未曾投拍的《魂归离恨天》。

《小儿女》(1963)
她完结的九个电影剧本中有六部改编自外国文学/电影著作——它们都在英美被拍成了电影,张爱玲更可能是在美国经过看电影触摸到了它们,她与赖雅婚后常去看电影(拜见司马新著《张爱玲在美国》),连影片《魂归离恨天》所本的艾米莉·勃朗特名著《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张爱玲曾表明自己那时还没看过原著,剧本分场和好莱坞1939年威廉·惠勒导演、劳伦斯·奥利佛、曼儿·奥白朗、大卫·尼文的浅显剧Wuthering Heights简直相同」(引自符立中著《张爱玲的电懋年代》),剩余的三部中一部是续集著作且有别人原著,两部原创中还有一部是为女星度身定做。

《南北喜相逢》(1964)
即便如此,上述《六月新娘》中仍留有张爱玲的惯性与细节;假如咱们不把原创当作仅有显贵的编剧法,那些借来的、沿用的或定做的故事里仍有评论的空间:它们不光在方法技巧的层面展示了她叙述「我国化」乃至「香港本土化」故事的才干,也在主题和内容上凸显了她一向的一起视角与真诚关心。
简略粗犷地说,「外国电影」(张爱玲此刻多中意于改编自英国戏曲的英美电影)是她的编剧法,而「我国人」是她永久的主题学。《六月新娘》里麦勤和汪丹林的对话像是对此精粹而逼真的演绎:当「外国电影」(注:张爱玲《六月新娘》剧本中汪丹林说的是「美国电影」)遇上「我国人」,既有相似共通的场景姿势,又要有「实践上不是这么回事」隐微教导。

《六月新娘》(1960)
1957年的影片《情场如战场》是张爱玲在电懋公司的榜首部上映著作,历来也被以为是她电懋时期的榜首部编剧著作。香港研究者冯晞乾考证,张爱玲抵美后完结的首部剧本是1958年上映的《人财两得》,「依照她与宋淇协议的工作计划,张爱玲的确应该先写《情场如战场》,但由于参考资料没有到手,便只好趁空档编《人财两得》。

《情场如战场》(1957)
那时是1955年11月」(拜见冯晞乾著《张爱玲的电懋剧本》)。不管哪部先写,张爱玲都借了现成的电影故事:《人财两得》改编自英国剧作家Roger MacDougall(1910-1993)的《To Dorothy a Son》,1954年英国拍照了同名电影,又叫《Cash on Delivery》;《情场如战场》改编自另一英国剧作家Terence Rattigan(1911-1977)广受欢迎的的戏曲处女作《French Without Tears》,1940年好莱坞拍照出电影版别。
关于自己在香江影坛的首部著作,张爱玲不会漫不经心、「能读不能写」的跨界书写焦虑大约是她「借」剧本的缘由之一。影片《情场如战场》上映后,一连三周,盛况空前,打破了几年来香港国语片优越卖座记载,这让张爱玲松了一口气,她在1957年7月14日致邝文美的信中说:「《情场》能够卖座,自各方面考虑,我都能够说『干了一身汗』,由于我也觉得人家总拿咱们这种人当坐而论道的墨客。」

《情场如战场》(1957)
《French Without Tears》的故事产生在一个成人法语训练校园里,几个志在成为外交官的英国学生在此学习,其间一个学生的妹妹Diana和房东的女儿Jacqueline的参加使得这个小国际里情海生波。《情场如战场》里的两位女主角被设置成姐妹——身世殷实之家叶纬苓与叶纬芳,故事环绕她们打开。
张爱玲将原作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平移到了《情场如战场》中,纬苓对应Jacqueline,纬芳对应Diana。电懋公司力捧的女星林黛扮演妹妹纬芳,她美艳娇俏、性情生动外向、好胜心强,到哪里都是必定的主角,她以搜集男性寻求者为乐,却又捉弄他们,让他们诙谐为难、丑态百出,是片中种种笑料的肇始者;但她并不是女权榜样,她只管自己风头出尽,对姐姐一点点不让,清楚不喜欢小职工陶文炳却要强占究竟。
可最终,这个放到我国的新旧品德中都不能安身的爱情大玩家却没有得到一点赏罚,结局仍旧让她固执追逐自己的爱人。纬芳除了身份变为叶家二小姐,性情与业绩都沿用了她的西方原型Diana。

《情场如战场》(1957)
但《French Without Tears》的场景设置在校园,那里多是聚散之间的故事;张爱玲将《情场如战场》的主角们集合于家庭,就为看似忽然的情感铺设了长长来路。《French Without Tears》中提醒Diana成为「独身公害」的原因是她毫无安全感,她既承受平凡身世带来的心思自卑,又分担着整个年代给予年青人的怅惘心情,她不断结交男友、需求他们却又轻贱他们,以此缓解乃至抵挡本身的自卑与怅惘。
她在最终宣称Alan是她的真爱,观众也只能权且一听;而在《情场如战场》中,固执的纬芳总算示弱,率直自己一向爱着表哥榕生,就有着与原作不同的含义:他们严密的亲戚联系不光增强着这份表达的可信度,一起也意味着纬芳长时间处于情感的不满足与压抑情况,而这就能够成为她屡次游戏爱情的内涵原因。
也便是说,关于这样纬芳这样一个难容于新旧品德的「坏女人」,对表哥长时间隐忍的爱就能够成为她固执行为的救赎。张爱玲创造性的身份改写缓解了故事的逻辑窘境和笔下人物的品德窘境,将之变成我国群众心照不宣的故事。

《情场如战场》人物联系图
影片《六月新娘》的故事学习自Terence Rattigan编剧的另一部著作《While the Sun Shines》,1947年在英国拍照成电影。那同样是一对未婚配偶大婚前的跌宕故事。

《六月新娘》(1960)
两剧的人物与情节根本相同,连男主角的家丁都相同油滑狡黠。但后者的叙事重心落在男主角即未婚夫哈普敦伯爵(The Earl of Harpenden)身上,他收留了来自美国的醉汉马尔维尼中尉(Lieutenant Mulvaney),不久未婚妻在火车上结识的法国人科尔伯特中尉(Lieutenant Colbert)也找上门来,舞女克拉姆Crum则一向是他家的常客。
跟着未婚妻伊丽莎白(Elisabeth)及其公爵父亲The Duke of Ayr and Stirling,一个依托女儿的败落贵族的到来,哈普敦不光是在情感上,还有他的工作出路都面临了检测。Terence感喟更多的是已成帝国斜阳的贵族阶级,他们到了张爱玲笔下就变成旧日在上海富有过的世家,这刚好符合那些年风云变幻之下的部分我国人的实践。
《六月新娘》是为行将出嫁的女星葛兰打造的,影片结束葛兰扮演的汪丹林披上婚纱,证婚人宣告成婚日为1960年6月15日,葛兰的实践成婚日就定在1961年的同一天。张爱玲天然要应和这一要求,况且翻来覆去的女儿心思本便是她的拿手。

《六月新娘》(1960)
她从头分配故事次序,隐忧轻愁、一差二错、捣乱爆笑地一路讲过去,她带着「你在国外不会懂」的自傲,着重爱情中的「我国性」,用中外差异掉包阶级不同,交出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团圆故事。汪父的性情设置沿用原作中的公爵,却又清楚是文华影片《不了情》中虞家茵父亲的连续:他仍旧自私、败家又贪财,落魄了就拿女儿当摇钱树,爱充局面动辄自卖自夸。
但他走过的路远超虞父,那些由上海至香港至日本又至香港的脚印背面有特定的我国历史;在华裔和游子集合的场合,他就分疏出我国内部的地域性,他的自省分外到位「人家是不考究表面,不像咱们上海人便是空架子」,让给观众又感叹又亲热。张爱玲初入文坛时就有在中西之间写作的自觉,乃至免不了自我东方化的夸大;将外国电影改编成我国人的故事,她公然深谙其道。

《六月新娘》(1960)
《桃花运》和《小儿女》是张爱玲电懋时期的两部原创电影剧本,它们比不得她小说的杂乱弯曲、意象杰出、意蕴深远;也比不得她之前改编的外国电影多属神经喜剧,用夸大、偶然、重复、反差结构全片,让观众即时过瘾;它们是呈给「广阔的观众」的浅显剧,在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中评论现代我国人的人伦。这样的写法倒与张爱玲的小说最为挨近,只不过是粗糙简略版了。这两部影片所聚集的夫妻、爸爸妈妈与子女,是张爱玲历来的关心点。
1959年上映的影片《桃花运》是张爱玲为电懋编撰的第三个剧本,这个故事像是张爱玲1947年编剧的影片《太太万岁》的续集或变奏,影片原名「负心汉」恰对应着「太太万岁」。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该剧,只说:「这出戏里的噱头虽欠好,是我自己想的,至少不会犯重。」时移世易,她的野心从《太太万岁》时的「用技巧来替代传奇」缩小到了这儿「不犯重的噱头」。

《太太万岁》(1947)
《太太万岁》中老公的「桃花运」仅仅全剧的一部分,到了《桃花运》中却成为故事的悉数。老公杨福生成为榜首主角,故事环绕他情迷歌女丁香打开。但观众很快发现,张爱玲实写老公,虚写太太瑞菁,后者以灵通的理性掌控大局,她才是全片的魂灵人物。
瑞菁是与陈思珍相同的贤妻,且更为老练油滑,少了许多「好意办错事」的为难。在张爱玲的剧本中,直到第四场杨福生将歌女丁香举荐给妻子,瑞菁才正式露脸。即便露脸了,也是淡淡一笔:「瑞菁允许浅笑」后,随即离去,丁香只好对着她的背影恭维,「常常听人说起,都说杨太太分缘好。」
老故事在香港开端了新轮回。虽然在故事容量和叙事技法上,两部影片颇有距离,但从上海的胡同到港九的大街、从太太陈思珍到太太瑞菁,张爱玲展示与评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妇德」。她早年嗜看电影,决意「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咱们四周的风俗人情」,评论的便是两部「同样地触及妇德的问题」的影片《门生争春》与《梅娘曲》。

《太太万岁》(1947)
张爱玲对她所在年代思维情况的洞见便是:「妇德的规模很广,可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老公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如此的「妇德」要求能够包括进她后来称之为「五四遗事」的名目下。她思索与评论的起点是一向结实而强壮的男性中心的社会实践,女人要怎么在这新旧稠浊的年代自处?
与《太太万岁》有意
抛弃「传奇」相对照,《桃花运》强化浅显剧中的「传奇性」,它传达中年男性观众与年青女人相恋的潜在等待,也给予女人观众一个白日梦式的中年主妇传奇:大度睿智的妻子总算挽回了老公。瑞菁的成功过分润滑与顺利,作者关于妇德的反思与反讽消逝在传奇中,留给观众的好像是关于「妇德」的必定与赞赏。
好在影片结束,张爱玲总算让这个精良的妇德故事露出了一点漏洞。当心回意转的老公转而疼爱妻子赠予歌女的金钱,瑞菁却宁可从头赤贫:「把钱送光了,再回到钻石山开个小饭馆,你当大师傅,我当女招待,只需你肯吃苦,咱们再从头干起。」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中,悬置着瑞菁的哀怨与无法:只需这社会仍是男性中心,再「精良」的妇德也只能当令化解危机,终不能免于危机。
处理完了「老公」的问题后,「母亲」又出了情况。1962年,女星尤敏与母亲因金钱问题对簿公堂,这多少折损了她纯洁可人的玉女形象。宋淇力邀张爱玲为尤敏量身定做影片以弥补,因此有了次年上映的影片《小儿女》。

《小儿女》(1963)
影片中尤敏扮演的王景慧献身自己、抚育幼弟的情节与实践中艺人尤敏鼓励养家、供弟读书的现实两相衬托,真假交叠、里应外合地打造出尤敏善解人意、勇于承当和献身的圣女形象,相较于之前芳华无敌的玉女形象,这个具有了美德的圣女形象更能赢得遍及的怜惜与好感。
这部受命之作源于实践日子中尤敏的「母女联系」,而「母女联系」在张爱玲生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方位。她与母亲的共处堪称是一种「伤口体会」,母亲给予她的那些琐碎的尴尬,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点地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她说:「母爱这标题,像全部大标题相同,上面做了太多滥调文章。……其实有些爱情是,假如把它戏曲化,就光剩余戏曲了,母爱尤其是,」她打破母爱的神话,而代之以「审母」的置疑目光去观照人间的母子/母女联系。《小儿女》这一以父亲续弦为主线的影片,叙述的却是怎么做「母亲」。

《小儿女》(1963)
具有慈父及两个灵巧幼弟的少女王景慧与旧同学孙川相恋,孰料父亲也在此刻与女同事秋怀有成家计划,幼弟以为行将失掉姐姐与父亲而反响剧烈。景慧抛弃了爱情,持续行使长姐的母职……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王家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暴露了问题。
影片《小儿女》中的王家母亲亡故多年,实践上却是全片最重要的人物,以缺席的在场者——或许说是鬼魂——的身份统治着这个家庭、统治着小儿女们的情感国际。每个家庭成员对缺席母亲的无限感念,使这个失母的家庭看似幸福地凝聚在一起。

《小儿女》(1963)
她好像不同于张爱玲小说中刻画的那些恶母形象,她由于「太好」而成为全片挥之不去的鬼魂。对母亲的忠实则成为阖家的崇奉。两个幼子将零花钱省下来买了两盆花,一有空就到母亲坟上去。那里成为他们最安全且最留恋的「子宫」,也是他们最遵循忠实的所向。
秋怀得到孩子们的体谅,要在大雨夜里赶往他们母亲的坟场才干完结,一如承受鬼魂的坟场托孤。在影片中,幼弟的「恋母情结」不仅仅构成于旧日的母子共处中,父亲与姐姐景慧也参加了过后促进的队伍。

《小儿女》(1963)
生者与死者一起刻画了「戏曲化」的滥情的母爱——这正是张爱玲从前批判的。影片描绘出了这种「不散的阴魂」及其「情感独裁」的结果:弟弟们不是情感独立的孩子,姐姐为此差点献身爱情,父亲也在鳏居多年后坦言「人不能靠回想过日子」。
这全部假如是正面和夸姣的话 ,为什么会折损父亲的日子以及姐姐的爱情?影片收尾在医院产生的「大团圆」,王家姐弟总算承受了秋怀。但张爱玲又用小孩心性的幼弟抢秋怀哨子、景慧对她一向称号「李小姐」的细节暗示着这种「承受」的含糊不稳,她的为母之路负重致远。

《小儿女》(1963)
总归,在那些张爱玲编剧的电懋影片中,在那些相似外国电影的我国场景里,她常常经过叙事与细节说着「实践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在她书写的我国人独爱的「大团圆」里,她仍是要经过叙事与细节说着「实践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一个编剧的才智与技巧,都能够在这句话里见深浅和凹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