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部片,在华语电影现已到顶了
近日,网络上关于某知名明星的传闻再次引发热议。多位网友纷纷曝光其私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涉及的内容包括未公开的恋情、工作中的不当行为等。这些“黑料”虽然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对于公众形象的影响不容小觑。随着舆论的发酵,该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波及其事业发展,引发更多讨论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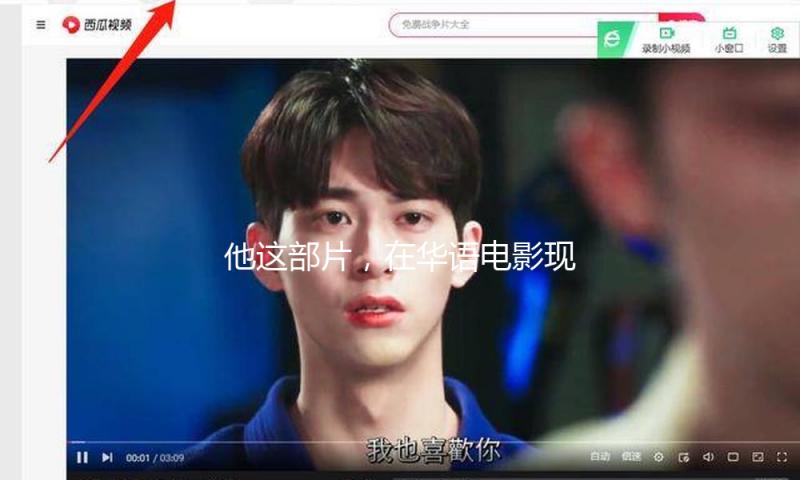
刘起
杨德昌没有人比更愤恨,也没有人比他更柔软。
一系列敌对的特质,以一种旗鼓相当的方法,出现在《逐个》中。
浪漫与实际、哀痛与欢喜、冷漠与火热、怜惜与嘲讽、单纯与老成、愿望与油滑、说教与静观、理性与理性、既置身其中又抽离于外。这些异质性元素的磕碰,带来了一种杂乱的调性,成果了杨德昌的独特性。

《逐个》(2000)
很少有一部著作能像《逐个》相同,在文本主题层面,出现出这样多层次、多面向的维度。
许多人喜欢《逐个》,认为这部著作像人生相同,体现了人生各个阶段。可是,这不过是一个最简略、最轻松的判别。这种判别只会滑向一种理性的、自怜自哀、自我投射的感受,关于了解《逐个》的深度起不到任何作用。
《逐个》包罗万有地展示了人生松懈又琐碎的全貌。影片结束,敏敏慨叹「人生哪有那么杂乱」,NJ说「你不在的时分,我有时机过了一段年轻时的日子,原本认为我再活一次的话或许会有什么不相同,成果仍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再活一次的话,如同真的没那个必要」。
洋洋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这些诗意且抒发的人生感悟,最简略取得一种情感共识,但也最简略遮盖《逐个》的社会维度与考虑深度。

了解杨德昌的要害,在于其著作活跃介入社会的意图。杨德昌是解析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情况的最谨慎、杰出的剖析家。
《逐个》回绝以一种朴实抒发的方法来出现人生。杨德昌之所以成为杨德昌,就在于他在抒发的诗意之外,总是维持着一种尖利批评的间隔。这种更为疏离化的情绪,使其有进退维谷取得一种关于台湾当下社会的深入体恤与尖利对质。
《逐个》如同一个真相转机的缩影,以一种全景式的出现方法,深入地反映出台湾这个东亚儒家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社会日子的对立与存在的问题。
《逐个》中每个成年人的人生窘境,都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今世都市人的特有境况。《逐个》出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国际中,社会的剧烈革新关于个别生命经历的影响和改动。
NJ的人生窘境,来自于社会规矩关于人的劫持与形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NJ,一直是一个缄默沉静的男人。在日本一处静寂的公墓,NJ总算向阿瑞道出了多年前他脱离阿瑞的原因,他爸爸妈妈和阿瑞都期望他学工程学,但没有人关怀他自己的主意。这种无法挑选自己人生轨道的苦楚,也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暗影。

洋洋和NJ
观众能在NJ 身上,看到杨德昌自己的生命经历。杨德昌先学了工程并从事计算机职业,后来才转向电影。
这是今世东亚社会进入现代化时的某种社会实际,一般我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爸爸妈妈,都会要孩子挑选一个能敏捷挣钱的职业,比方科技、医药、法令或金融。我国人传统的实用主义,在现代社会,就体现为对孩子人生规划的功利性。
阿弟人生的荒唐剧,也来自于社会转型期一种新与旧的拉扯。阿弟的前女友芸芸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现代女人,也是他的作业同伴,与绮年玉貌未婚先孕的小燕构成一种反差。而阿弟那非常具有戏曲作用、起起落落的出资生意,也来自于他含糊的协作理念——前现代的情面联系/现代商业社会的生意规律。

阿弟
在NJ妻子敏敏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对立性。
敏敏是公司高管,一个典型的女强人,但当她遇到波折(母亲昏倒)时,却紧张无助,只能求助于传统的宗教——上山静修。在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场景中,也能看到现代与传统(规范的现代化作业流程与黄道吉日)的割裂:敏敏一边以机械化的高效方法处理作业业务,一边说「我弟弟说,昨日是这一年杰出的一天,所以我妈妈不会有事的」。

敏敏
传统的东亚儒家社会的人际联系,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消解和推翻。
NJ的协作同伴以一种商业利益为准则进行人际交往。他们对大田的情绪体现了这种利益准则。而NJ身上,保存了那种前现代的情面联系,「大田是个好人,你们不能这样对他,你们这样很伤」。NJ的理想主义与单纯,也是他与这个社会方枘圆凿的原因。
杨德昌的著作,一直在评论个别与真相、与社会的联系。《牯岭街》中,杨德昌的姿势是对立、不退让的,这种愤恨在结束激化为小四刺向小明的那一刀。

《牯岭街少年杀人工作》(1991)
在《独立真相》和《麻将》里,仍然是杨德昌对这个冷漠、自私、荒唐、迷失的国际的一种批评,他仍然愤恨。可是,《独立真相》结束再一次翻开的电梯门,《麻将》结束马特拉与纶纶在街头的重逢,却留下一个宽和的进退维谷,带来一丝温暖。

《麻将》(1996)
到了《逐个》,杨德昌如同与这个国际宽和了。但灵敏的观众不难发现,杨德昌仍然保存了对这个国际的批评和嘲讽,困难是以一种温文的情绪。
《逐个》的美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本的深度,来自于杨德昌关于国际的杂乱情绪,一种带着批评的宽和、一种混杂着嘲讽的怜惜。这种对立性,带来一系列异质性元素的磕碰,一起又取得了一种调和,使《逐个》如万花筒一般,又深又美、既杂乱却又无比清楚。
戏曲vs.电影
杨德昌在方法与美学层面,有一个不断改变的进程。前期《海滩的一天》和《恐怖分子》,带有激烈的现代主义美学风格——远间隔的、抽象化的深层视角,一种安东尼奥尼式的批评客观主义。

《恐怖分子》(1986)
《牯岭街》庞大的主题,杂乱的叙事结构和许多的人物,比较挨近史诗的叙事。
赖声川这之后,杨德昌跟做了一段时间的戏曲,所以,就不难了解《独立真相》和《麻将》的场景、对白和叙事结构的戏曲性。赖声川的《乱民全讲》和杨德昌的《独立真相》有某种相似性,都是今世台北的都市挖苦剧。

《独立真相》(1994)
《逐个》回归到干流的庞大叙事传统,以一种情节剧的结构来结构故事。从方法上看,《逐个》既是戏曲性的,又是高度电影化的。
朱天文说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发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电影的特质是抒发的,而非叙事和戏曲」。与此相对,杨德昌更倾向于叙事。《逐个》中,NJ、敏敏、阿弟、婷婷、洋洋——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一条完好的叙事线。
经过一种精细杂乱的叙事结构、准确高效的情节设置,将多条情节线并置。并经过照应、变奏、镜像的方法,在多条情节线之间重复切换。这种高度理性的叙事方法,是杨德昌与许多亚洲导演的规模大不同。而抒发的成份,就像是在谨慎叙事结构中活动的空气。
怜惜vs.嘲讽
从他的一切著作中,都能清楚的看到,杨德昌是怎样一个言辞尖利而心里温顺的人。对讨厌的人物,他能在批评时保存一丝怜惜;对喜欢的人物,他也能美妙的限制他的热心。比方《独立真相》中,油滑奸刁的小凤,自有一种爽直妥当;单纯仁慈的琪琪,也有一种优柔寡断。
《逐个》从始至终,杨德昌都保存了他作为创作者怜惜且嘲讽的杂乱情绪。困难他尽量抑制不流显露这种嘲讽,咱们多少仍是能察觉到。比方在婆婆昏倒的哀痛时间,阿弟一边哭一边说,「我算过,今日是本年杰出的一天,妈妈不会有事的」。
说教vs.静观
杨德昌常被诟病的一点在于他的说教。的确,杨德昌的每一个人物都像哲学家,喋喋不休的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对国际的观点。如同每个人都能宣布一番哲理性的深入见地。八岁的洋洋说,「咱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工作?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散布,这样不就有一半的工作看不到了吗?」

可是,长风万里观众只看到这个层面,我只能说太惋惜了,你把杨德昌与那些心灵鸡汤作家划了等号。
其实,杨德昌的诱人之处,恰恰在于他用对白消解对白,用说教反抗说教。当每个人物喋喋不休的讲着人生哲理,许多声响被并置于一处,终究就只留下相同——幽静。
比方对日子的情绪。敏敏在对昏倒母亲倾诉的进程中,发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我每天讲的都一模相同,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几分钟就讲完了。怎样只要这么少,我觉得我如同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相同,我每天在干什么?」每天重复的上班族或许对敏敏的话颇有感受。

可是,大田却说,「每一天都是首位次,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同一天不进退维谷重复过两次。」
比方对艺术的情绪。「电影创造今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从前至少延长了三倍,在电影里边得到的日子经历至少是咱们自己的日子经历的双倍」。迷影青年很简略在这句话里找到共识。但其实杨德昌是带有挖苦意味说出这句话的。说出这句话的人物胖子,终究用电影中的方法——杀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
这让人想到张爱玲写的,「日子的戏曲化是不健康的。像咱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明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像,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企图经过电影中的经历来代替人生的经历,就会发生一种反讽作用。
长风万里不能领会杨德昌的人物言语中包括的杂乱性宽和构性,就无法真诚了解杨德昌。

说教的意图是要灌注一种理念,是明晰告知观众作者的理念,杨德昌却并无此意。《逐个》中,杨德昌如同讲了许多道理,告知观众许多人生哲思,但这其实更像是一种挖苦,令人想起《麻将》中红鱼所说,「每个人都等着他人告知他该怎样做」。终究,杨德昌用这种众声喧闹的方法来抵达静默——一种审慎的静观姿势。
在这一点上,杨德昌与侯孝贤途径不同,却异曲同工。
沉溺vs.抽离
侯孝贤的印象,有一种近乎天性的生命力,许多著作都是其本身生命经历的累积和发酵。
杨德昌则不太相同。困难在《牯岭街》和《逐个》中,咱们都能看到杨德昌片面生命经历的投射,但他是以一种理性的考虑和高度技巧化的结构,来出现自己的生命经历与感悟。这种对生命经历的书写方法,使作者能够取得一种既置身其中又抽离的姿势。
从个别的生命经历中抽离出来,以一种检讨、批评的姿势来调查,就有进退维谷取得一种结构性的力气,从个别性进入社会性。詹姆逊在剖析《恐怖分子》时,就敏锐的发现杨德昌的这一特色——「社会的总体性是能够被感知的,但如同要从外部」。
喜剧性vs.悲剧性
《逐个》以婚礼作为最初、以葬礼作为结束,这个整齐对称的结构再简略显着不过,称不上有什么美妙之处,一个平凡的创作者能很简略照搬这个结构。

杨德昌关于结构的准确掌握,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沉稳地以一种辩证联系来开展叙事:将喜剧性和悲剧性美妙而又杂乱的混合在一起。杨德昌将人生悲欣交集的杂乱况味,用一种清楚的叙事来出现。
他如此拿手转调,总是能在一个欢喜的瞬间,轻盈的滑向哀痛,又或许在一个哀痛的局面中,遽然参加某种荒唐性的喜感。阿弟在看着重生的婴儿时,不可思议就哭了起来。这个瞬间,便是咱们的人生啊——一种像是欢欢又像是悲痛的感觉。
还有一些异质性的元素,也被统一在《逐个》中,构成了一种既坚持又调和的美妙感。
比方浪漫与实际。NJ二十年后对阿瑞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人」。从前,我讪笑这句情话,觉得这种浪漫虚伪的近乎错觉。

尤其是NJ回到家,疲乏的对妻子说,「长风万里再重来一次,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个情节如同告知咱们,杨德昌更信任日子的实际。可是,当我今日重看《逐个》,遽然觉得,杨德昌对那句话同样是毫不怀疑的。

比方温顺与暴戾。杨德昌的愤恨,在著作中,必定会被具象化为一个暴力工作,这也是凶杀工作贯穿其著作头绪的原因。《恐怖分子》《牯岭街》《麻将》与《逐个》,都以一次凶杀作为结束。
比方单纯与老成、愿望与油滑。杨德昌所沉迷的主题——个别与真相的联系,往往会被出现为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的个别与其所在环境的抵触。
《牯岭街》中的小四、《独立真相》的琪琪、《麻将》的纶纶、《逐个》中的NJ和洋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人物。在这些核心分子周围,则是一些不再纯真、自私荒唐的「社会人」,他们的老成油滑,更衬托出主角的方枘圆凿。
《逐个》是集大成者,出现出杨德昌的理性思辨力气,以及一以贯之的批评和自反。
《逐个》如此清楚冷静,困难更温文,但由于一系列异质性元素的并置,使其更深入和更有启发性。就像导演借洋洋之口说出的给「给人们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杨德昌不只体现人物说的东西,也体现他们没有说的东西;不只体现人们是什么样,还体现日子是什么样。他会站得离他的人物更远一些,更多地把他们看做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
比起《牯岭街》,《逐个》中他的愤恨和挖苦,困难少了,但更准确和抑制,惋惜这成为他最终一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