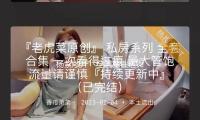留念诞辰100周年丨奥康纳:倾听鲜活生命的低语与呼吁 — 新京报
近日,网络上再次掀起了一阵关于某知名明星的“黑料”风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根据网友们的爆料,相关人士似乎在个人生活中存在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无疑让公众对明星的形象产生了新的思考。无论结果如何,此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关注信息来源,保持理性分析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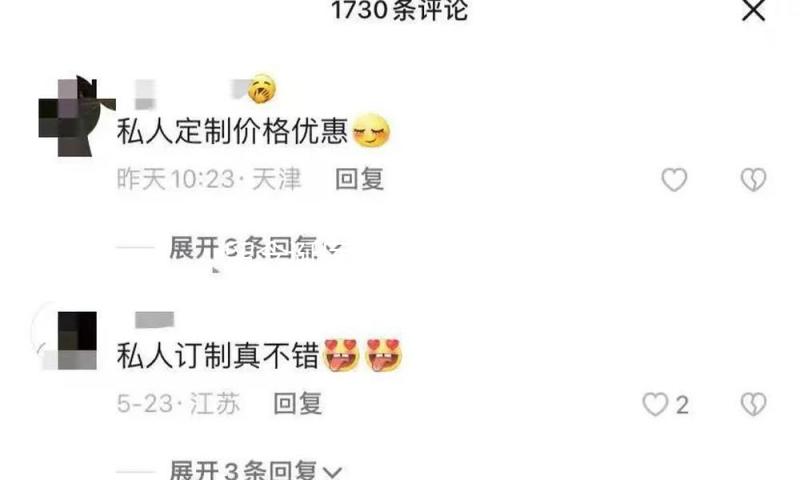
100年前的今日,1925年3月25日,弗兰纳里·奥康纳出生于美国南边佐治亚州的萨凡纳,1964年因病逝世,只存在了39年。在其短短一生中,奥康纳写出两部长篇小说、31个短篇小说,关于一位作家来说,这个数量算不上多,但这些极具原创性、带有激烈荒诞感和宗教意味的著作已足以让她留名后世,在美国南边文学中与威廉·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并排。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1925年3月25日—1964年8月3日),美国作家。1951年被确诊患有红斑狼疮,1964年逝世。出书长篇小说《智血》《暴力攫取》,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和《上升的悉数必将集合》,书信集《生计的习气》等。
撰文 | 田颖(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美国谈论家门肯(H. L. Mencken)在《艺术的撒哈拉》一文中宣称,美国南边“在艺术上、心智上和文明上像撒哈拉沙漠相同,是一片穷山恶水。”门肯宣布此番言辞不久,他对南边如此果断的结论被一场重要的文学运动推翻。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南边出现了大批超卓的作家,他们用细腻的笔触书写着南边的人与物。南边并非瘠薄之地,而是滋补这批南边作家集体的膏壤。在这三十年间,南边文学厚积薄发,迎来了美国文学史上的“南边文艺复兴”。
南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是美国“南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界的“宠儿”。作为“20世纪以来最超卓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奥康纳用著作成果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威望。在时间短的文学生计中,奥康纳一共创作了2部长篇小说和31个短篇小说,宣布了很多的谈论文章和杂文。奥康纳逝世后,她的影响力还在不断连续,美国社会各界以各种方法留念这位超卓的南边女作家。1972年,后人为奥康纳撰写的《短篇小说全集》(Complete Stories)获小说类美国国家图书奖。自1983年起,佐治亚大学出书社每年都会颁布“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2015年6月,美国邮政总局为问候奥康纳发行了留念邮票,这是美国“文学艺术”系列的第30枚留念邮票。2023年,奥康纳的生平故事被拍成了电影《野猫》(Wildcat)。2024年,奥康纳的未竟之作《异教徒为何愤恨?》(Why Do the Heathen Rage?)出书。
奥康纳的著作为何如此备受推重,乃至在她逝世多年之后还有如此很多的拥趸?这个问题能够在她的讲演辞中找到答案。1952年,奥康纳受邀在乔治敦宣布了题为《新教南边的天主教小说家》(“The Catholic Novelist in the Protestant South”)。在讲演中,奥康纳道出了自己写作的奥妙,她以为“南边作家与南边规划大的枢纽是他的耳朵,它一般很敏锐……一个南边人物一旦开口说话,不管他在日子中处于什么位置,咱们都能听到悉数南边日子的回声”。在奥康纳一百周年诞辰的今日,咱们无妨当一回听众,一同倾听这位美国南边女作家的故事。

弗兰纳里·奥康纳。
以鸟为伴:闻鸟识情。
1925年3月25日,奥康纳出生在美国南边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父亲爱德华·奥康纳(Edward Francis O’Connor)和母亲莉加纳·克林(Regina Cline)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后嗣,奥康纳是这个天主教家庭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对她心爱有加,身为房产经纪人的父亲终年出门在外,家中业务主要靠母亲一人承当。在童年时期,父亲人物的缺席和母权认识的强化造就了奥康纳活络、独立、背叛的特性。这样的家庭日子对她影响至深,她与爸爸妈妈相对疏远的联系也投射到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中。
1937年,奥康纳的父亲患上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难以治好的缓慢免疫系统疾病。次年,年仅13岁的奥康纳随家人搬到米利奇维尔。作为旧日佐治亚的州府,米利奇维尔带有稠密的旧南边气味,这让性情叛变的奥康纳倍感不适。奥康纳的青春期随之而来,以往安静的家庭日子被打破,她首位次体验到日子的无常。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指出,13岁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重要阶段,“大约在13岁,男孩子们阅历了真诚的暴力见习,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成为他们的权利毅力和对竞赛的喜好。而就在这时,女孩子抛弃了野蛮的游戏。”其时的奥康纳正处于这一重要的年龄阶段,她不只面对青春期的苦恼,还得应对家庭日子的突变。
好在,奥康纳自有纾解压力的方法。在她全家人搬到米利奇维尔之前,1934年经市议会投票,米利奇维尔被划归为“鸟类保护区”。这里是鸟的天堂,也是调查各种稀缺鸟类的抱负之地。初来乍到的奥康纳从中找到了独归于她的趣味,她喜欢与鸟相伴,视鸟为至交。列传作家布拉德·古奇(Brad Gooch)在《弗兰纳里·奥康纳传》(Flannery: A Life of Flannery O’Connor, 2009)一书中,借奥康纳表亲之口,叙述了她初到米利奇维尔时的景象:“记住其时我正在格林街门廊前荡秋千,弗兰纳里牵着一只矮脚鸡走过,那是我开端对她的回忆。”除矮脚鸡之外,奥康纳还养了一只名为“阿梅利亚·厄尔哈特”(Amelia Earhart)的鹌鹑,乃至贴心肠为它缝制了短裤、白衬衫、夹克。1941年,奥康纳的父亲病逝,这给了她很大冲击。在以鸟为伴中,奥康纳的青春期仓促完毕了。
1951年,26岁的奥康纳被确诊出和她父亲相同的病症红斑狼疮。其时,她已在美国文坛锋芒毕露。为了缓解病痛,奥康纳重拾少女时期的喜好,在家中养了“一只独眼天鹅、一群绿头鸭、三只日本丝羽矮鸡、两只波兰冠鸡、一栏雉鸡、一栏鹌鹑”。说起她对鸟类的酷爱,奥康纳坦言“起先仅仅是一种温文的爱好,后来却变成了一种热心,一种寻求。”在很多鸟类中,奥康纳深受喜欢孔雀,听说她曾养了一百多只孔雀。

弗兰纳里·奥康纳,1962年。
红斑狼疮发生时,奥康纳的臂膀和关节会痛苦、肿胀。病痛的摧残钝化了她的身体,却让她的听觉变得活络。奥康纳尤爱倾听孔雀的叫声,在题为《鸟中之王》(“The King of the Birds”,1961)的散文中,她记录了自己与孔雀为伴的那一刻:
雄孔雀常常会在抬起尾巴的一起,也进步它的叫声。它好像经过自己的脚接纳到了来自地心的振荡,这振荡经过它向上传导,得到开释:唉-喔-咿!唉-喔一咿!这声响,在郁闷者听来便是郁闷,在歇斯底里者听来便是歇斯底里。关于我,它听起来总像是在庆祝一个看不见的游行。
当孔雀鸣叫时,奥康纳听到的是“看不见的游行”。那一刻,听觉的在场代替了视觉的缺位。倾听者奥康纳经过拟声文字“唉-喔-咿”,传达了她身为作家的想象力。诗人艾略特把这种具有创造力的听觉感官称之为“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听觉想象力是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这种感觉深化到有认识的思维和情感之下,使每一个词语充满活力:深化最原始、最完全忘记的底层,回归到源头,带回一些东西,寻找起点和结束。”如此说来,孔雀的鸣叫声成为奥康纳感知情感的载体,作家的活络和天分让她能够“闻鸟识情”,借孔雀鸟鸣的拟声来出现、书写她的情感和感悟。正如列传作家古奇所言,“她经过她的鸟儿来表达自己的心里国际。”。

《生计的习气》,作者:(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译者:马永波,版别:新星出书社 ,2012年3月。
南边之声:万物自生听。
身患重疾的奥康纳由于行动不便,很少走出美国南边,生于斯长于斯的她把“听觉想象力”融入自己的写作中。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以为:“每一件文学著作首先是一个声响的系列,从这个声响的系列再生出含义。”对奥康纳来说,这个声响系列是她对美国南边的书写。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五言绝句诗《咏声》中写道:“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在这首富含道理的小诗中,声响中的一静一动乃国际万物的运转规则。奥康纳天然没有读过唐诗,但她长于凭借声响来讨论生命、精力和崇奉等文学母题。在文学著作中,经过声响来出现的景色即音景(soundscape),它“是声响景象、声响景色或声响布景的简称。”(傅修延《听觉叙事研讨》)在奥康纳的文学国际里,音景具有叙事的功用,众声喧闹,汇成“南边之声”。

《好人难寻》,作者:(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译者:於梅,版别:新星出书社 2020年5月。
在短篇小说《河》中,就有一个以音景为主的细节。故事环绕南边小男孩儿阿什菲尔德(Harry Ashfield)打开,年幼的他不被爸爸妈妈关爱,一次偶然的时机,他参加了在河滨举办的一场宗教仪式。在牧师的声声呼唤中,小男孩儿获得了心里的安静。奥康纳在小说中写道:“他[牧师]声响转而变得柔软而悦耳:‘一切河流都发源于那条河,并终究汇入那条河,就像条条江河汇入大海……水慢慢地流动,和我脚边陈旧的红河河水流动相同慢……’”。牧师的布道声与潺潺流水声稠浊在一同,人声与天然之声合二为一,构成一道具有南边地域特征的音景。
众所周知,美国南边气候湿润,河道是当地常见的景象,这正是故事的发生地。“河”除了是南边标志性的地域景色之外,还有多重象征含义。美国南边历来保存,深沉的宗教传统和价值观根植于南边文明中,因此南边也被称为“圣经地带”(the Bible Belt)。在基督教文明里,“河”意味着逝世、洗礼、救赎和重生。在小说结束,小男孩儿单独走入河中,想为自己施洗,却不幸溺亡。如若将小说中的这个音景放置在南边文明的语境中来解读,牧师布道声与水流声的交融是南边哥特风格的具象化,整个场景充满了荒诞、奥秘的气味,这为故事凄惨剧的结局埋下伏笔。

弗兰纳里·奥康纳,1947年。
短篇小说《仁慈的乡间人》则从人道的视点来出现音景。奥康纳用娓娓道来的口吻,叙述了发生在南边小镇的爱情故事。南边姑娘乔伊学识渊博,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童年时,她不幸遭遇了一场事故,失去了一条腿,不得不装上了一个木制假肢。乔伊虽饱读诗书,但身体的残损让她怯弱、自卑。乔伊与母亲住在南边乡间,很少与外人往来。一个外来小伙儿曼利·波恩特(Manley Pointer)上门推销《圣经》,他为人热心大方,咱们都叫他“仁慈的乡间人”。瘸腿的乔伊很快招引了曼利,他策画怎么才能让这位单纯的南边姑娘落入爱情的圈套。小说的高潮发生在曼利与乔伊在草垛上约会时,他用声响引诱涉世未深的乔伊:“他[曼利]的口气新鲜、香甜,像孩子相同……他喃喃地说着他爱她,对她一见钟情,但他的呢喃像是被母亲哄睡的孩子的梦中梦话。”在南边炙热的阳光下,躺在草垛上的乔伊听到如此动情的表白,情不自禁地投入曼利的怀有。但是,音景是景象,也是布景和幕布。“将音景称为声响幕布,是由于它像幕布相同能够用于掩盖与遮挡”(傅修延《听觉叙事研讨》),它的遮盖功用会掩盖说话人的真挚目的。在悦耳的情话背面,隐藏着曼利昏暗、歪曲的心里,他的温顺表白好像海妖塞壬迷惑的歌声,被这个声响引诱的人终将难逃厄运。当乔伊沉醉于曼利的情话时,曼利趁其不备扔掉了她的假肢,拂袖而去,独留她在高高的草垛上。故事结局的反转让读者措手不及,虚假的曼使用极点的手法撕碎了乔伊最终的庄严,她的残肢和破碎的自负同时暴露在耀眼的日光下。在这个极具挖苦意味的故事中,音景是赋有张力的存在。当曼使用声响引诱乔伊时,仁慈与凶恶、单纯与油滑、纯真与浑浊之间的抵触都掩盖在音景的幕布之下。
奥康纳的著作承继了南边文学的哥特传统,她自己因奇怪、病态的文风而引起谴责。当群众质疑她笔下荒诞、残损的人物时,奥康纳回应道:“关于近乎耳聋的人,你要大声喊叫;关于视力不清的人,你要画出大而惊人的人物。”由此可见,奥康纳经过扩大感官,来刻画各类人物。在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智血》(Wise Blood, 1952)中,奥康纳凭借夸大的音景,刻画了一个小角色——初到城里的年轻人伊诺克(Enoch Emery)。一次,年仅十八岁的他参加了与大猩猩握手的活动,“这是他到这座城市以来首位只向他伸出的手。它显得那么的温顺。”伊诺克意外发现,这个备受欢迎的大猩猩竟是由真人身披兽皮假扮的。他从中遭到启示,把偷来的兽皮套在身上,站在公路旁边,等候世人和他握手:
它(伊诺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好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干。后来才开端大声呼啸,一边吼一边拍胸脯,又蹦又跳,不断地挥动臂膀,脖颈伸得老长,折腾个不断。刚最初的时分,那呼啸并不明晰,可没过多久,吼声就越来越大了。一瞬间消沉可怖,一瞬间尖厉吓人,来回重复,最终戛但是止。
这段对声响的描绘阴沉、恐惧,让人读后难免心头一惊。裹着兽皮的伊诺克没有比及与之握手的世人,可怕的叫喊声却吓跑了公路旁边的一对情侣。细细品味以上引文,咱们能够发现,伊诺克仿照大猩猩的叫声是从静态到动态,最终又归于静态,这刚好印证了韦应物的诗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伊诺克起起落落的叫声除了烘托出南边哥特小说可怖的气氛之外,好像也在悲叹这个小角色的凄惨命运。

《智血》,作者:(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译者:蔡亦默,版别:新星出书社 2010年7月。
以上对文本的解读不过是“井蛙之见”,奥康纳对声响的巧用远不止于此。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奥康纳为安在写作中如此注重对声响的感触?从日子经验来看,“听”往往先于“看”。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见王熙凤时,王熙凤的进场是“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与“看”比较,“听”的感知触角延伸得更深、更远。对奥康纳来说,她的身份是两层的,她既是“南边之声”的倾听者,也是叙述南边故事的人。“听”与“说”的内容都依靠声响来传达,“音”成为联合“说”与“听”的前言。在《鸟中之王》的文末,奥康纳写道:“从池塘、谷仓和房子周围的树丛里,我就会听见庆祝的合唱声响起:勒-呦 勒-呦,迷-呦 迷-呦!唉-呦 唉-呦,唉-呦 唉-呦!我计划坚持下去,让孔雀繁衍,由于我坚信,到最终,我能听到的最终的话便是它们的叫声。”奥康纳把孔雀的叫声比作“庆祝的合唱声”,她倾听的不啻是声声鸟鸣,更是鲜活生命的低语与呼吁。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今日,很多信息超载的视频画面充满于现代日子中。在地铁、轿车和大街上,随处可见行色仓促的人群只管静心刷屏,“失聪”的现代人已无暇静心倾听。偶然,咱们无妨将手中的电子产品放置一旁,像奥康纳相同,去倾听万物之声,体悟“听觉的想象力”带来的热心与感动,这或许正是这位南边女作家留给咱们的启示。
撰文/田颖。
修改/张进。
校正/赵琳。
上一篇:固体力学家黄克智院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