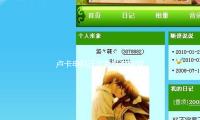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小津安二郎的光影世界
近日,某知名人士的背后故事引发广泛关注,众多网友纷纷对于其过往经历进行探讨。随着相关信息逐渐被曝光,部分不为人知的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黑料”无疑为公众提供了更多了解该人士的视角,同时也让大家对其形象产生了新的思考。究竟真相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揭晓。

小津安二郎(1903-1963)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在长达35年的导演生计中,他阅历了无声电影年代与彩色电影年代,导演了包含很多无声短片在内的54部影片,保存至今的有36部。一般以为小津电影多从家庭切入,体现庶民的喜怒哀乐,所以也有小市民电影之称。小津于1962年取得日本艺术院会员称谓,这是日本电影界首位位获此称谓者。

小津安二郎
小津电影二十次当选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影片”,其间六次当选首位名、两次当选第二名。当选年度十佳首位名的六部影片是《我出生了,但……》(1932)、《心血来潮》(1933)、《浮草物语》(1934)、《户田家的兄妹》(1941)、《晚春》(1949)、《麦秋》(1951),其间前三部是无声电影,由此可知小津在1930年代已是日本闻名导演之一。当选年度十佳第二名的两部影片是《父亲在世时》(1942) 、《东京物语》(1953)。

《东京物语》海报
1958年,《东京物语》在英国伦敦电影节上映,取得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1923-1994)等英国电影人的高度点评,被授与“富于构思”的“萨瑟兰奖”。尔后,美国、欧洲各地开端连续上映小津电影,小津电影在欧美电影届逐步声名鹊起。2012年,英国电影协会杂志《视与听》(Sight and Sound)评选史上最巨大的一百部影片时,小津代表作《东京物语》取得导演类别首位名。
一
在小津电影乃至日本电影走向国际的进程中,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1924-2013)的尽力功不可没。唐纳德·里奇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小喜爱电影,结业于俄亥俄州莱马中心高中,二战时从军,1946年22岁时,以驻日美军文明部打字员身份驻守日本3年,在此期间他为一些英文报刊编撰了一些影评等,显现了必定的文字天分。在其时的战胜国日本,唐纳德·里奇这样默默无闻的美国战士触摸到了英美闻名的日本研讨家、美国高级将领以及川端康成、铃木大拙等日本文明名人,令其视野大开。1949年唐纳德·里奇回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29岁时大学结业,翌年再度赴日,尔后长时间为日本英文报刊《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编撰影评、书评等,还一度在早稻田大学教学美国文学,一起致力于日本电影在西方的传达作业。
1959年,唐纳德·里奇与约瑟夫·安德森合著《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一书,该书成为英语国际首位部研讨日本电影的著作,也是欧美日本电影研讨必读书目之一,其间的小津部分是英语国际有关小津电影的最早研讨。唐纳德·里奇的代表作还有《小津安二郎的美学》(1978年)、《黑泽明的电影》(1979年)等。在其不懈的尽力之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的电影成功进入了西方“国际经典电影”的批判领域。
唐纳德·里奇一生致力于日本电影在西方的传达作业,在日本居住了60余年,2013年死于日本东京,享年88岁。唐纳德·里奇的人生与日本及日本电影业形成了某种共赢联系,当年的美国战士成功逆袭为文明名人,日本电影也成功地进入了西方“国际经典电影”谱系。为感谢唐纳德·里奇为日本电影传达做出的巨大贡献,1963年日本电影海外遍及协会及日本电影作者连盟约请其从当年开端担任“日本电影海外遍及协会”参谋;1983年日本川喜多留念电影文明财团授与其“首位届川喜多奖”;2004年日本#授与其旭日勋章。旭日勋章是日本授与“对国家、公共有劳绩者、有引人瞩目的明显功劳者”的奖项,可见唐纳德·里奇在二战后日本形象重塑过程中发挥的效果。
二
当今西方的小津研讨并未脱离唐纳德·里奇当年建立的批判结构。例如,唐纳德·里奇在上世纪70年代点评小津:“在他的同胞心目中,是一切日本电影导演中富有日本特征的一位。他一生的电影,只要一个首要的体裁,即日本的家庭,并且只要一个主题,那便是家庭的溃散……(唐纳德·里奇《小津》,连城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09年P1)。”
相似这样的点评方法简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从英语国际传向非英语国际,必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惯性表述。唐纳德·里奇从剧情、拍照、剪接等视点进行研讨的形式也被承继了下来。鲁承临曾在《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讨简史》一文中,对英语国际小津安二郎的研讨进行过讨论,其文写道:
伴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研讨的学院化和规范化,西方学界关于小津的研讨多发生自电影学或是美学的视点。具体说来,首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小津当作日本电影乃至日本文明的标志,从文明论或许民族符号的视点对其解读,另一个则是把小津的电影当作老练的电影制作而归入国际经典电影的事例进行剖析……换言之,关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评论家,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也能够一起满意两种学术爱好,一种是充满了对东方文明的猎奇心态,另一种则是对电影的叙事、款式的改变更有爱好的学者。(鲁承临《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讨简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6期P68)
鲁承临将西方的小津研讨大致概括为“对东方文明的猎奇”及“注重电影的叙事与款式”两个方向,即“电影学”或“美学”研讨方法。实际上,这两种研讨方法与唐纳德·里奇的小津研讨一脉相承,而国内的小津研讨大致上也是这种叙事形式的延伸,呈现了一个通过西方滤镜的小津形象——哀婉而富于审美内在。但是,对我国研讨界而言,研讨的起点需求洞悉小津作为侵华日军的身份问题,并且仍是一名侵华毒气军队的日军。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阅历?血腥、残酷、逝世气味必定如影随形。那么,哀婉而富于审美内在的表述方法就显得有点荒谬了。
三
小津电影与战役及日本战胜领会的联系现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论题。田中真澄早在20年前就出书了《小津安二郎与战役》(みすず书房,2005年)一书,具体梳理了小津的战役阅历,一起收录了小津参与侵华战役时期的“战场日记”(《阵中日志》),成为21世纪小津研讨不可或缺的列传材料。尔后不久,我国学者顾铮宣布了《侵华战役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书城》2007年第8期)一文,指出小津电影是“脱节战役梦魇的尽力”,顾铮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他的电影,或许便是以关于日子的深化刻画来脱节战役梦魇的尽力。他关于人道、关于日常的看似安静的探求,或许并不能阐明他关于人的决心,也不能阐明他关于自己的决心。这或许只能阐明,心灵现已大荒芜的他,通过关于本身与别人的了解,尤其是通过战役炼狱之后,所发生的对掌握人道的丰富性的根本上的不自傲。而咱们将他的电影与他的战役阅历结合起来看,也更能领会人道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振幅与回旋余地。
顾铮的表述要言不烦,却颇能切中要害,“心灵大荒芜”问题的提出值得沉思。但是,顾铮的文章并未遭到应有的注重。尔后,马晓雁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战役》(《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中,持续讨论了相关论题,但并未充沛打开。
小津一生中有过两次深入的战役领会,首位次是以侵华日军毒气军队伍长身份(相当于班长),参与了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间长达22个月的侵华战役的阅历。第2次是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长达两年7个月的东南亚战役阅历,这次他是以日军报导部电影班成员参与日军宣扬电影拍照作业。1945年8月,小津在新加坡迎来日本战胜日,随日军屈服成为战俘,1946年2月被遣送日本。
值得注重的是其首位次长达22个月的侵华阅历。1937年9月初,小津应征入伍,从属上海差遣军直属野战毒气军队,9月24日小津随军队乘轮船从大阪动身,3天后抵达上海参与淞沪会战,尔后其军队从苏省镇(今镇江)到扬州、仪征、六合、滁县(今安徽滁州)等地(『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5),制作了各种惊天惨案。小津在193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所属毒气军队在江西修水河战役中施行毒气战的具体情况,这与中方材料的记载共同。
小津的“战场日记”展示了侵华日军“心灵荒芜”的一面。但关于同胞老友,他好像仍然“有情有义”。导演山中贞雄(1909-1938)生前是其老友,两人先后参与侵华战役,但山中贞雄于1938年死于河南开封日军野战医院,令小津咬牙切齿。小津于1939年7月退役回国后不久,就到京都大雄寺祭拜了山中贞雄,还担任了《山中贞雄剧本集》(1940年)的装帧作业。同年,大雄寺内建立“山中贞雄之碑”,小津编撰了碑铭。田中真澄指出小津于1951年导演的《麦秋》是一部赠与亡友的安魂曲(『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9)。
实际上,包含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东京物语》在内,小津电影的重要特色是重复呈现逝世与葬礼的场景。在《户田家的兄妹》(1941)、《父亲在世时》(1942)、《宗方姊妹》(1950)、《东京物语》(1953)、《早春》(1956)、《东京暮色》(1957)、《小早川家的秋天》(1961)等影片中,逝世或葬礼如影随形,乃至成为了小津电影的一种标配。
加藤典洋从小津电影中读出了浓浓的“战胜”气味,指出小津电影的主人公们说话口气温文,常常垂首低眉地喝酒,茫然地浅笑,且大都溜肩,稍微低着头(加藤典洋『敗者の想像力』集英社,2017年P24)。他把小津主人公们的这些特色归结“战胜”气质,以为小津电影便是凭借着这股浓浓的“战胜”气味取得了日本观众的共识——这是小津与日本观众之间的一种秘而不宣的心灵共振。不仅如此,加藤典洋以为“失利感”是一种遍及的人类情感,这也是小津电影走向国际的真诚原因。实际上,加藤典洋提醒了小津电影的一个隐秘——一种隐而不宣的政治气味。

《东京物语》剧照
四方田犬彦愈加注重小津电影中频频呈现的逝世或葬礼场景,他在《小津安二郎——不在之映像》(《今世电影》200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关于那些在小津著作中赶到病危者的床旁探望病人的进场人物来说,所谓逝世,并不是一个不管做出何种献身都应当逃避而又难以被逃避的灾祸,倒不如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应当照实承受的事态的发展过程。看看《东京物语》便可了解,往往整部著作都是以这种逝世为重心轴打开的……谁想想看都会理解,将小津的著作作为超卓地描写了日本传统家庭的溃散的影片加以欣赏是看走了眼。”
一切阅历过的必将留下遗痕。作为从前参与侵华毒气军队的日军战士,退役后的小津不断拍照逝世与葬礼的影片归于道理中事。挥之不去的战役暗影构成了小津电影的深层逻辑,是时分从头审视小津的光影国际了。